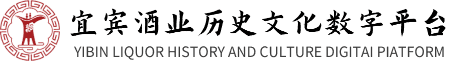宜宾有酒的历史可从考古发掘和史料记载中得知,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向家坝水电站规划淹没区的发掘中,叫化岩遗址出土的陶酒杯成为4500年前宜宾地区有酒的实物证据。史料记载也证实了这一事实,《史记》记载汉时“独蜀出枸酱,经夜郎行销南越”。在宋元伯的《酒小史》“南粤食蒙蒟酱”中,蒟酱被作为酒的类型记载。当代学者凌受励根据史料论证蒟酱并非酒,而是一种用包括酒、肉、麦曲、香料、盐和“枸”果实制成的酱类食品,只是含有大量酒成分。同时,民间酿制用于家庭饮用的粮食酒“窨酒”。唐时宜宾称戎州,杜甫流亡四川时曾经此地,留下诗篇《宴戎州杨使君东楼》;“重碧巧春酒,轻红擎菊枝。楼高欲愁思,横笛未休吹”,这是明确提到戎州“重碧酒”的诗篇,“重碧酒”是唐代戎州盛产的春酒。明清时期,叙州府的酿酒走出家庭酿制的局限,发展起数家大型酿酒手工业工场,明初以“温德丰”、“长发升”最为有名,至清代同治年间已有“利川永”、“长发升”、“张万和”、“德胜福”等多家酒坊。在历代酒业经济的基础之上,民国时期宜宾酒业经济走向了新的高度,出现名酒“五粮液”。
(一)秦汉时期焚道地区酒业的兴起
(1)窨酒、蒟酱
秦时,巴蜀二郡的界线大概划在江阳(今泸州市)与僰道(今宜宾市)之间,僰道属蜀郡,居民是蜀人的一支。蜀人酿酒历史悠久,《华阳国志》云:“九世有开明帝,始立宗庙,以酒曰醴,乐曰荆”。在宜宾多次出土绘有酿酒图、酒肆图、宴饮图的汉代画像砖、画像石等,又印证了汉代此地酿酒、饮酒之风盛行。
秦汉时期,僰道酿酒,以民间“窨酒”和“蒟酱”为主。窨酒,是用谷物蒸煮后自然发酵再储藏于泥土之中酿制而成的低度酒,与当代醪糟酒相似。酿制方法后世有详细说明,《富顺县志》记载:“制法取糯米一斗,蒸熟用冷水过,晾于大框,俟微温,和以麴末,贮缸中,拍米使平,自面至底中空一凹,如碗大。举缸坐草窝中,周围严覆厚被以待汁出。经日,汁满去被松窝养至六七日,并糟贮于罈,渗以高粱烧酒,用泥封固,每年如是。增注:一次罈满为度曰酿糟酒;年远成琥珀色或封至百数十年者味尤浓厚曰窨酒”,民间多采用此法酿制这种酒精度数低的“窨酒”。《西蜀平蛮全录》载“明日重阳节,蛮俗赛神,……今大雨如注,必放心也饮酒,正可出其不意”,从材料可知,居住在焚道地区的少数民族酿制并在平时饮用“窨酒”。这种习惯延续至今,现在宜宾地区各家各户都有酿造和饮用醪糟酒的习惯,已成为宜宾地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
元宋伯元在《酒小史》中载“南粤食蒙蒟酱”,将蒟酱作为酒记载;《史记》记载;“独蜀出枸酱,经夜郎行销南越”;《华阳国志》也记载,僰道有蒟;明周洪漠曾述:“独蜀出蒟酱……而历代郡志皆谓蒟酱出自长宁”;在雍正《四川通志》及嘉庆《四川通志》中提及叙州府物产时皆载:“蒟酱,史记所载蒟酱即此,各属具出”。当代酒文化研究学者凌受励先生实地考察了当今依旧留存蒟酱腌酱方法的屏山县龙华、真溪地区,证实老君山附近盛产的“拐枣”即蒟酱的主要原料“枸”。故可肯定的蒟酱确实产于本地区,唯一存在争议的是蒟酱到底是酱还是酒?凌先生据史料论证蒟酱并非酒,而是一种用包括酒、肉、麦曲、香料、盐和“枸”果实制成的酱类食品,但含有大量酒成分。不管蒟酱是否是酒都肯定了这一时期焚道地区存在酒的事实。如果蒟酱本身是酒,那么蒟酱就是这时期僰道地区存在的酒品。如果蒟酱只是一种含酒的酱类食品,那么蒟酱中所加的酒便先于蒟酱存在,依然可以证明僰道地区酒的存在。
(2)秦汉时期焚道地区酒业经济的特点
秦汉时期僰道地区流传的酒品呈现三个特点:
1.酿造技术简单,酒精纯度较低。僰道地区居住的先民用可得到的原料(稻米、粟),采用简单的发酵方式酿造出供祭祀或者饮用的日常饮品,酿造规模不大,且酒精度数低。
2.窨酒并没有流入市场售卖,主要供自家宴饮之用。这一时期的酒因为酿造规模以及用途等因素的影响,并不具备上市销售的条件,主要是家庭自酿自用。
3.蒟酱曾作为特产向朝廷进贡,汉代以后酒税又成为政府征集的税务。据记载:“天汉三年,初榷酒酤。”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的酒税是根据国家财政的需要,届时全国酿酒规模扩大,汉武帝征战对国家财政有极大需求,酒税可对财政起到补充作用,故而此后酒税成为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以看出,秦汉时期,焚道地区已经大量存在家庭酿酒,饮酒风尚的较早兴起,为后世宜宾地区发展酒业提供了可能性和可行性。
(二)唐宋以来戎州酒业逐渐发展壮大
(1)重碧酒、荔枝绿、姚子雪曲
宜宾酒业在唐宋时期有较大发展。一方面得益于酿酒工艺的进步,以往酿酒是以果实、粮食蒸煮,加曲发酵,压榨后出酒,唐宋时期酿酒工艺改进,将“压榨”改为了多次过滤。最大的突破是对酒精的提纯,戎州酒业在全国酿酒发展大背景下得到很大程度的提升,注重过滤,改变所酿酒的颜色和口感。另一方面得益于一些文人志士对戎州酒的宣传,出现了“重碧酒”“荔枝绿”“姚子雪曲”等名酒。
诗人杜甫因安史之乱离开长安入蜀,永泰元年(765年)六月经戎州时,仰慕杜甫己久的时任戎州刺史杨使君在戎州城内东楼宴请杜甫。杜子美吟唱了《宴戎州杨使君东楼》:“胜绝惊身老,情忘发兴奇。座从歌妓密,乐任主人为。重碧巧春酒,轻红擘荔枝。楼高欲愁思,横笛未休吹”。据《梁溪漫志》载:“叙州,本戎州也。老杜戎州诗云:‘重碧倾春酒,轻红擘荔枝。’今叙州公酿,遂以‘重碧’”,可知重碧酒是为戎州“郡酿”。据时节来看,六月所饮之酒,应是当时的春酒,“重碧”酒是多次重复酿制的窨酒,称为重酿酒,是经过滤去了渣子的清酒,类似今天的米甜酒,只不过是经过多次重酿而成。“碧”为青绿色,其所呈现的颜色是由重酿的次数决定的,重酿的次数越多酒就越清澈。
两宋时期,开始细化酒的管理制度,在四川通行的是榷曲制度和万户酒制度。据记载:“川陕承旧制,卖曲价重,开宝二年,诏减十之二。既而颇兴榷沽,言事者多陈其便,太平兴国七年罢,仍旧卖曲”。地处偏僻的地方多为榷曲区,叙州列属于榷曲区。政府只控制了曲的专卖,买曲酿酒是合法行为,这为包谷、高粱产量较大的叙州府大肆酿酒提供了便利。戎州酿酒业空前发展,出现了“荔枝绿”“绿荔枝”“姚子雪曲”等名酒,戎州酿酒的产量随着西南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大有增加,酒税在财政税收中地位上升。
这些名酒之名多得于宋代大诗人黄庭坚,宋哲宗时黄庭坚因党争被贬涪州别驾,其间为避外兄之嫌,迁至戎州。绍圣四年(1097年)六月,黄庭坚到达戎州并在此居住长达两年半,留下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几乎每首不离酒,堪作宜宾酒史资料的诗词就有七首。七首诗词就出现了六个酒名,即:荔枝绿、安乐(姚子雪曲)、松醪、玉醴、清醇、春泉。元宋伯仁《酒小史》所列全国名酒中,就收录了戎州王公权的“荔枝绿”和廖致平的“绿荔枝”酒。而这两种酒名就来源于黄庭坚的《廖致平送绿荔枝为戎州第一、王公权荔枝绿酒亦为戎州第一》。王公权是黄庭坚好友,家酿“荔枝绿”酒很有名。关于黄庭坚口中廖致平家的“绿荔枝”是指酒还是指他家的荔枝尚有争议,可据黄庭坚手迹《明瓒诗卷题后》“元符三年七月,涪翁自戎州溯流上青衣,二十四日宿廖志平牛口庄,养正治酒弄芳阁,荷衣未尽,莲实可登,投壶弈棋,烧烛夜归”来看,黄庭坚曾至廖的家中见证了他家有酿酒的事实以及廖家雄厚的财力,自家酿酒是可能的。“姚子雪曲”被认为是五粮液酒最成熟的雏形,相传为宋代戎州绅士姚氏家族私坊酿制,采用玉米、大米、高粱、糯米、荞子等多种粮食酿制而成,也是宋代叙州名酒之一。黄庭坚在《安乐泉颂》中颂扬姚子雪曲的美妙及除湿功效:“姚子雪曲,杯色增玉。得汤郁郁,白云生谷。清而不薄,厚而不浊,甘而不哕,辛而不螫。老夫手风,须此神药。眼花作颂,颠倒淡墨”。锁江安乐泉位于今宜宾锁江石附近,“锁江主人能治酒”,姚氏取以酿酒,黄庭坚认为所酿之酒清而可口,饮用后令人感觉很安乐,故命名安乐泉,还作颂一首。所姚子雪曲和安乐泉都是姚氏所酿酒的酒名。
此外,宋代长宁军酿制的兵厨酒也是叙州名酒之一,因是军中兵厨所酿,故名“兵厨酒”。这种酒取嘉鱼泉的水,嘉鱼泉在长宁县,是一口古井。井内水池沸腾,如串串葡萄,此起彼伏,故又名葡萄井,至今仍在。泉水酿酒,酒尤清别,《长宁县志》载:“其泉夏冷冬温,汲之酿酒烹茶味极甘美”。
(2)唐宋时期戎州酒业经济的特点
唐宋时期戎州酒业获得较大进步,酿酒技艺的改进使得酒的产量和销量都有了长足发展。据这一时期的酒品来看,酒业经济发展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酿酒原料种类增加,酿造技术进步,注重酒精度的提纯,酒的质量提高。此前,酿酒原料以稻、黍、秫米为主,而宋代却扩大到秔、糯、黍、秫、粟、麦等多种原料,其中尤以小麦为主;酿造技术也由原来的蒸煮、曲酵、压榨改为蒸煮、曲酵、多次过滤,“重碧酒”“荔枝绿”等重酿酒与窨酒相比最大的进步就在于酒精度数的提纯。
2.酒品种类增多,戎州出现享誉地方的名酒。“荔枝绿”“绿荔枝”“姚子雪曲”的出现,是戎州酒业发展的重要表现,也推动了全国酿酒业发展。
3.中央王朝对四川酒税制度细化,酒税在财政税收中的地位提升。酒本不是生活的基本必需品,而且在唐宋酿酒多用粮食后,存在与民争食的弊端。所以,政府一方面通过禁止私酿维持百姓对粮食的需求,另一方面官榷酒税又能补充国家财政,可以说这两大举措既解决了与民争食的问题,又扩大了财政收入,无疑提升了酒税在国家财政体系中的地位。
4.戎州酒走出家庭宴饮的格局,在市场上销售并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西南地区经过了秦汉以来的政治经略和开发,社会经济有了较大发展,戎州与西南少数民族多有来往,至宋代开始与少数民族地区的贸易市场上售酒,极大地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三)元明时期叙州酒业持续发展
(1)烧酒、杂粮酒
元代酿酒业最大的贡献就是开始推广烧酒,烧酒又名白酒,它是一种用蒸馏法制成的酒,酒精纯度较高,在今天,人们往往把高粱制酒称作高粱烧,麦、米、糟等料制成的烧酒称作麦烧、米烧或糟烧。据李华瑞先生《中国烧酒起始探微》观点可知,酿制烧酒的历史并不像《本草纲目》的记载“自元时始创其法”,而是唐宋时期已经开始使用蒸馏技术酿制烧酒。这不仅改变了酿酒的方法,也提高了产量。但关于叙州酿酒却在唐宋时期多次过滤的“重酿酒”为主,故推测至元才引进蒸馏技术酿制烧酒。后《富顺县志》记载“高粱酒……名为泡酒亦曰烧酒,岁产总额约一二万斤”。《南溪县志》中“干烧”“常酒”“烧酒”“老酒”“大曲酒”也都是蒸馏法酿制的白酒,据此可知叙州地区也采用蒸馏技术酿制烧酒。
至明,统治者放松酿酒业管制,全国酿酒业开始大规模复苏并且发展,叙州酿酒业在大政策下也开始重新发展起来。明朝初年,叙州人陈氏继承了姚氏产业,总结出陈氏秘方,酿制杂粮酒。此酒两名,文人雅士借黄庭坚诗句称之为“姚子雪曲”,下层人民叫“杂粮酒”,被认为是今天五粮液的直接前身。明代叙州酿酒曲酒为盛,分大曲酒和小曲酒,杂粮酒是大曲酒中的一种,酿制过程与大曲酒基本相同,主要区别是原料的不同:大曲酒以高粱作为原料,而杂粮酒是多种粮食(高粱、大米、糯米、玉米、麦子、黄豆、胡豆等)混合酿制。大曲酒类的口感和酿造,相当依赖酒窖,窖老而醇香,清同治年间,出现了四家著名的酿酒坊:利川永、长发升、张万和、德盛福,这四家酒坊共购置和保存了明初以来所建的12口酒窖。其中“德盛福”与“长发升”酒窖最老,德盛福有明代弘治年间酒窖四口,长发升有明代成化年间酒窖五口。经考证这些酒坊都曾酿制“杂粮酒”,长发升尹氏所酿杂粮酒仅供自家饮用,其他酒坊有见于市,但各家酿制杂粮酒的配方各异,并没有形成谁的专利。现如今在五粮液酒业集团的“501”车间依然保存着明朝的酒窖并持续使用,明朝酒窖的继续使用是酿造五粮液的重要条件之一。而流传下来的大量古酒窖也正好说明,明代叙州酿酒事业的兴盛。
此外,2011年,四川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考古队对岷江河畔公馆坝的牛口驿糟房头进行考古发掘,后经四川省和全国两次专家认证,确定宜宾红楼梦糟房头酒坊是明代白酒酿造作坊遗址,是四川第一次发掘出使用年代最早、最单纯、要素最全的明代白酒酿造遗址,这不仅证实了明代叙州酿酒的规模,也肯定了叙州所酿之酒的品质。
(2)元明时期叙州酒业经济的特点
元明时期,因蒸馏技术的引进,酿酒业发展更为繁盛,元代叙州酒业因为战乱并没有得到充分发展,至明时,国家政策的变化以及农业经济的复苏,给叙州酿酒业提供了发展机遇并给后世叙州酿酒业打下了坚实基础。这时期叙州酒业呈现出如下特点:
1.元代蒸馏技术的推广,后世叙州地区多采用此法酿制烧酒。虽然战乱时期叙州酒业没有创造和发展的大势头,但家庭酿酒却有创新,马可·波罗于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从云南返大都的途中,经过滇东北、川南僰人地区时记载:“……居民以肉、乳、米为粮,用米及最好香料酿酒饮之”,叙州地区的居民开始在酿制的酒中加入香料,这与今川南地区制作窨酒以枸杞、桂花、橘皮甚至天麻、人参作辅料相符合。
2.大型地穴式酒窖的形成是明代叙州酿酒业的重大进步,大型酿造酒坊形成,叙州酿酒业形成规模性生产。牛口驿糟房头的考古发现是叙州明代酒窖最真实的展示,其中发掘出的称为“头等是三百六十斤”长方体石块,经专家鉴定为称量的秤砣,三百六十斤的重量可见这个糟坊酿酒的繁盛。
3.明代叙州酒已大规模销售,酒坊“前店后坊”的规模已经显而易见,成为叙州酒常见的销售模式,出现一大批著名的酒坊。
(四)清代宜宾酿酒业的发展
(1)曲酒、杂粮酒
明末清初,宜宾因为奢崇明、大西军与清军以及吴三桂叛军之间的战争相继进行,人口锐减,民不聊生,社会经济遭到空前破坏,宜宾几乎成为空城。民国《南溪县志》载:“天启初,奢崇明攻陷城邑,焚毁屠戮,瞩目皆瓦砾之场。”天启元年(1621年),四川永宁宣抚司宣抚使奢崇明叛明自立,燃起战火,在宜宾境内和明军几次交战,给当地造成了极大破坏。崇祯十六年(1643年),张献忠大西军攻到宜宾,烧杀抢掠,使当地人口迅速减少。南溪县“赤子尽化青磷,城郭鞠为茂草,一二孑遗远窜蛮方,邑荒废者十数年”“当时故家旧族百无一人存,人迹几绝,有同草昧”。这些战争给宜宾带来了毁灭性的破坏,叙州地区经济受重创,人口大规模减少。
为了充实四川人口,开发四川地区,清初实行“移民填川”政策,进行大规模的移民垦殖,“楚、越、闽、赣之民,纷来占插,标地报垦......时地价至贱,有以鸡一头布一匹而买田数十亩者,有旷田不耕无人佃种而馈赠他人者”,四川地区田园荒芜,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和江西等地的人民纷纷来开垦荒地。当时地价十分便宜,一只鸡、一匹布就可以买数十亩田地,有的土地所有者甚至将无力耕种的田地直接送给他人。大规模的移民开垦、轻徭薄赋和休养生息政策使得宜宾农业经济得到迅速恢复,“民获安居,修(休)养生意垂五十载……宇内宁谧,局粮未通,以粟易械,徭轻赋薄,时有减免,粟帛充盈,子性繁衍”。到雍正年间,“其时赋税徭之简,县庭争讼之稀,稻粱菽麦之饶,林木森林之畜,池沼田圃之广,衣食器物之朴,营缮建筑之便,百工佣价之低,童赢事亲之舒,戚党周遗之厚,婚姻交际之密,丧葬仪式之文,岁时宴聚之娱,春秋报祈之乐而有征”,宜宾农村经济又恢复了自给自足的状态。人民安居乐业,讲究礼仪,为酿酒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乾隆、嘉庆以后,当地的社会经济已经恢复到相当可观的程度,经过近百年的繁衍生息,人口大量增加,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叙州府户数为49874户;嘉庆十年(1805年),叙州府报十一县两厅为67950户,424215人;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叙州府已有489608户,1738584人。
由于明末清初的战乱,宜宾酿酒业处于停滞状态,急需资金输入和技术革新。清代前期,北方酿酒业以直隶、陕西、山西、河南和山东五省最盛,当时称为“北五省”。陕西是有名的踩曲造酒之地,在陕西关中产麦区,“民间每于麦收之后,不以积储为急务,而以踩曲为生涯,所费之麦不计其数”。民间收完小麦之后,并不储存,而是制成酒曲贩卖。咸阳、朝邑等县居民,“开设曲坊,伊等并不自己造酒,只踩成曲块发往外省”“踩曲之人则成群逐队,来往之客则结骑连樯”。陕西盛产高粱、苞谷等杂粮,亦有用杂粮酿制曲酒和制曲的丰富经验。陕西还有专门卖曲的曲坊,而且顾客很多,生意兴隆。当时四川绵竹用来酿造曲酒的母糟,就是从陕西略阳运来,而宜宾所用的母糟又是从绵竹转运来的。随着业务的直接或间接往还,陕西商人开始来宜宾经营酒业。后来籍隶陕西镶黄旗的年羹尧兼理川陕总督时,就曾从其所筹的云贵两省协饷银两中挪出一些款项在四川部分地方开设“典当”“曲酒作坊”和“钻探盐井”等,以安置来川求事的亲友故旧。其中辗转来到宜宾的,亦续有人在。当时四川民间流行这样的俗语:“皇帝开当铺,老陕坐柜台。盐井陕帮开,曲酒陕西来。”在宜宾城中经营曲酒的有北门“温永盛”、东门“长发升”和南门“德盛福”等。这些糟坊原有的明代老窖不仅恢复了生产,而且还开挖了新窖,扩大了生产规模。因此,宜宾的曲酒酿制业不仅在明代的基础上得以复苏,大规模的南北酿酒技术的交流更促使宜宾曲酒酿制技术朝更加精湛的方向发展,为五粮液的诞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关于清代宜宾酒业发展的状况可从部分材料中得到证实。一些史料将酿酒所用的苞谷和高粱与主粮相提并论,这不仅说明宜宾地区用高粱和荞麦酿制蒸馏白酒的事实,也可看出酿酒在叙州人的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比如,“谷之属,有粇(糠)有糯。粇者宜饭,糯者宜酒”,“苞谷,供食、饲豕或酒;高粱,酿酒或磨面作饼”。此外,南溪还有为酿酒而培育的新粮食品种,如“穬麦”,即油麦,叶细长而尖,实繁密,芒长似大麦,造曲或作马料”和“糍高粱,即酒米高粱,实如高粱,质程而泽,酿酒或磨面作饼”。
《富顺县志》还记载了糯米酒和高粱酒的酿制方法及产量:“糯米酒,制法取糯米一斗,蒸熟用冷水过,晾于大框,俟微温,和以麴末,贮缸中,拍米使平,自面至底中空一凹,如碗大。举缸坐草窝中,周围严覆厚被以待汁出。经日,汁满去被松窝养至六七日,并糟贮于坛,渗以高粱烧酒,用泥封固,每年如是。”“高粱酒,制法取高粱五斗或六斗,煮熟晾于泥地(俗称晾堂),俟微温,和以药麴,贮于箱上,覆草£,经一昼夜后和以老糟,贮木桶中用泥封闭数日后取出,入地甑蒸之,上盖营盘周围严密,不使气泄天锅在其上火发气腾凝为液体,以曲形锡枧引入罈中,名为泡酒亦曰烧酒,岁产总额约一二万斤。”可见,清代叙州府酿酒业已有相当的规模,曲酒分布范围扩大,种类增多。
随着酿酒业的发展,清政府还在宜宾地区征收了酒税,民国《南溪县志》和《富顺县志》对此都有记载。《南溪县志》载:“烟酒税:清光绪三十年奉设酒税局(在火神庙内),由县委绅经理,凡醩坊烤酒按觔征钱四文,以接口簿为据,每桶约出酒六十,征钱二百四十文。汇县易银,按季解,省嗣以收数零星不便,稽查改为月缴,计醩房双牌(七桶),月纳税钱一千四百五十文,单牌减半。三十三年经征局成立接收,仍由局委绅办理,宣统元年加倍征收,醩房双牌月纳钱税二千七百二十文,其局费历照百分之五扣支。”《富顺县志》载:“酒税,旧规每醩房一家由捕厅征收烧锅钱二千二百四十文,光绪二十九年总督岑春暄为济边练兵,饬办每酒一斤抽钱四文,宣统二年经征局册报,元年分实收银一万九千四百四十六两五钱零五厘(清末全年征税一云四万数千串)。”
虽然明末清初的战乱破坏了宜宾地区的社会经济,酿酒业也受到重创,但是清代前期的“移民填川”政策使宜宾的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粮食产量增加,酿酒业又重新发展起来,酿酒从业人数增加,酒业消费市场也逐步扩大,出现了“家家酿春酒,父老杂醉醒”的局面。从陕西输入的踩曲和酿酒技术,使宜宾的酿酒工艺有了很大提高,酒的种类和产量有所增加,清代后期政府还征收了酒税。杂粮酒酿制技术的改进,为五粮液的诞生提供了重要条件。
宜宾清代酿酒业继续发展,一些明代的作坊和酒窖继续沿用。同治年间(1862~1874年),由于天灾、战乱等原因,整个四川酿酒业开始转让兼并,“利川永”(原温德丰)“长发升”“张万和”以及“德盛福”等酒坊购置和保存了从明初以来的酒窖。
“利川永”原名“温德丰”。清代所酿酒为杂粮酒,杂粮酒的配方,是明初“温德丰”陈氏在高粱之外,掺和其他种类粮食混合酿制的,通过不断调配原料和各原料投入的比率,最终形成了流传后世的“陈氏秘方”。调配后酿出的酒,比单种粮食所酿的酒风味更佳,当时该酒没有命名,只称为杂粮酒。清咸丰年间,陈三继承祖业经营“温德丰”糟坊,亲任烤酒师。他通过长期实践,进一步完善了家传酿酒秘技“陈氏秘方”:“大米、糯米各两成,小麦成半黍半成,川南红粮凑足数,地窖发酵天锅蒸,此方传男不传女。”五种原料具体比例为高粱40%、大米20%、糯米20%、荞麦15%、玉米5%。他酿成的杂粮酒,是当时宜宾酒品中的佼佼者,以致后来城中传出了“北门窖子出好酒”的声誉。“陈氏秘方”丰富了白酒的味觉,它的产生是五粮液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清同治八年(1869年),赵铭盛继承“温德丰”,他扩大了酿造规模,继续发扬“温德丰”糟坊的工艺和风格,精心酿造杂粮酒。后来,邓子均与县属柳家乡兰登三联合购买“温德丰”糟坊,后改名“利川永”,酿制“杂粮酒”。利川永酒坊将曲酒与高粱白酒勾兑为“曲泡”,并在大曲酒中分段摘取“提庄”,民国时期行销海外。“长发升”,原生产土酒和大曲,后来自产杂粮酒为非卖品,只作自用或馈赠亲朋。因其为明代老窖所产,酒质特佳,店主曾自命名为“御用酒”,后觉不妥,仍称杂粮酒。“张万和”作坊位于北门外东濠街,销售门市在宜宾市小北街。糟坊的酒窖虽大都是清代中叶所挖,但因对明代老窖的借鉴和接近明初老窖的地理环境,以及酿技精良的工人,在少数酒窖中仍然酿出了取名“元曲”的上乘杂粮酒。德盛福,位于城区南门外走马街,前店后窖,这个酒坊在清代仍在生产。因其后人不得力,未能与“温德丰”糟坊同步发展。该酒坊以老窖所产“尖庄曲酒”最为著名,仅次于“利川永”“长发升”两家糟坊的质量。上述四家糟坊曾在明清时期的宜宾酿酒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后来进一步酿造五粮液奠定了坚实基础。
(2)清代宜宾地区酒业经济的特点
清朝时期,宜宾地区酿酒业发展迅速,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明末战争的破坏虽有所消怠,但随着“移民填川”政策的实施,农业经济复苏,粮食生产的增加又使宜宾酿酒业重新发展起来。
2.陕西人踩曲酿酒技术的输入,是宜宾酿酒业重新发展的技术支持,至今宜宾还流传着相关的民谣“皇帝开当铺,老陕坐柜台。盐井陕帮开,曲酒陕西来”。
3.“杂粮酒”的酿制为五粮液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杂粮酒在众多大曲酒中较为特殊,据民国《南溪县志》记载,同治九年(1870年)、光绪六年(1880年)、光绪十六年(1890年)高粱的价格分别是35、50、55;而同时期小麦的价格是40、46、50;黄豆的价格是50、60、66;绿豆的价格是50、56、56,可以看出酿制杂粮酒的原料多、成本高、工艺复杂,以至于虽酿制杂粮酒的酒坊多,但销售较少,如尹氏所酿杂粮酒就只供自家饮用。但用多种粮食酿造的杂粮酒却为后世五粮液的出现提供了经验。
4.在清代禁酒政策下,宜宾酒业却获得迅猛发展。一方面是由于商品经济发展使人们对酒的需求有了较大增强的原因;另一方面是由于国家政策在地方执行的过程中,地方官员弱化清廷的禁酒政策,他们用收取“规费”的方法来换取酒业经营的合法性。
5.杂粮酒酿造技术改进为“五粮液”酒的诞生提供了技术条件。曲酒酿造在这一时期得到陕西人酿酒技术的支持,叙州酿酒业大力发展,时至清代已有多家大型酿酒坊并存。
(五)民国时期宜宾酿酒业的发展
(1)五粮液
民国时期,宜宾酿酒业在前代的基础上继续发展,酒的品质不断提升。此时,宜宾的糟坊日益增多,酿酒业达到了相当的规模。
尤其是抗战期间,酿酒业快速发展,其税收成为国统区货物税的最大来源之一,整个四川酒业均为抗战做出了积极贡献。民国《南溪县志》记载了当时酒税的征收情况:“民国初改征收课办理,醩房双牌月纳钱三千六百三十六文;民国四年,京师创立烟酒公署,四川设烟酒公卖局,省划各分区设立分局,南溪隶于宜宾分局,设烟酒分栈,由绅商承认经理,缴纳金银一千六百元。酒税易钱为银分旺淡季,旺月每桶征银一元四角,淡月每桶征银七角……七年设监察员住栈管理牌照。十三年八月裁分栈经理,改设烟酒事务监察所,所长由省局委任,十六年改为包办,全年解烟酒税银一万圆。”《富顺县志》载:“至壬戌癸亥(1922、1923年),全县醩房四百九十一家,旺月约一千二百余桶,淡月六个月八百余桶,每桶高粱五斗出酒七十斤,全年出酒约三百余万斤。每桶每月征税三元五角,每斤五仙,全年征税四万二三千元。曲酒一家,杂粮酒七家,均在总数内,曲酒每斤征税三仙七星五,杂粮酒每桶每约月一元五角,每斤约税二仙一星五。
孙望山(宜宾著名酒商,新中国成立前任宜宾酒商业同业会主任)对宜宾的酒税也有记述,民国初大曲酒窖每个征2元,土酒桶每个征1元(系做一次缴一次)。1919年改为计斤征税,大曲酒每斤征税二仙七星五厘,小曲酒每斤征一仙二星五厘;按酒窖、酒桶来征收,具体算法是大曲酒窖分大(600斤)、中(400斤)、小(300斤)三种,酒桶则分大(200斤)、小(150斤)两种,照产酒数字发给凭单印照,规定酒只要出厂,不管内销还是外运,均要花票同行,印花贴在坛口边上,凭单由运酒人随身携带,如违反规定,除没收货物外,另处以5~10倍的罚金。1922年后,又调整了税率,大曲酒每斤征七仙二星五厘,小曲酒每斤征二仙七星五厘(按章依旧)。1935年改为按实计征,丈量酒窖的长、宽、高,算出酒窖的容积,规定每立方出酒4斤,按每年产酒8次(夏季停产40天)计算,12个月平均摊征。酒桶计征标准:桶口直径5尺,深3尺,算出容积,每立方产酒4斤,按每月产酒4次计征。1942年后,由于货币贬值,物价变化非常大,又改为从价征税,按出厂成本价的50%征收。
曾任叙州府隆昌县知县的清末民初时人周询对叙州府相当熟悉,他在《蜀海丛谈》描绘了当时川南糟坊酿酒的兴盛:“川省田膏土沃,民物殷富,出酒素多,糟坊到处皆是。私家烤酒者尤众”,“酒则各邑各乡,几乎家家皆能烤酿,直是一种最普遍之农民副业”。这正是民国时期宜宾酿酒业的真实情况。
宜宾城内的糟坊,临江而建,以取水方便为准则。因城中井水含盐、硝较重,杂质多,是不能用于酿酒的。金沙江和岷江水都是雪水、其江水澄碧,清纯无杂质,水质十分优良;但在选择用岷江水还是用金沙江水时,又大多决定用岷江水,因岷江与金沙江相比,汛期水变浑的时间较短,更胜金沙江一筹;故宜宾的酿酒作坊都是临岷江、金沙江而建,而大多汲水岷江。
民国时期宜宾城的糟坊共14家,都是生产大曲酒,沿岷江所建的糟坊有10家:鼓楼街“长发升”,有古窖16口;顺河街“利川永”,有古窖13口;顺河街“全恒昌”,有古窖7口;顺河街“听月楼”,有古窖6口;顺河街“刘鼎新”,有古窖14口;顺河街“天赐福”,有窖6口,抗战期间所建;东濠街“张万和”,有古窖10口;东濠街“钟山和”,有窖11口,抗战期间所建;马家巷“万利源长”,有窖10口,抗战期间所建;外北正街“吉庆”,有窖4口,抗战期间所建。沿金沙江所建糟坊4家:下走马街“德盛福”,有古窖8口;下走马街“赵元兴”,有古窖7口;南街“张广大”,有窖6口,抗战期间所建;文星街“吉鑫公”,有窖3口,抗战期间所建。
民国时期岷江畔喜捷到高场共有15家糟坊:在离喜捷不到2千米的公馆坝有徐氏槽坊头和胡氏槽坊。距公馆坝徐氏槽坊头不到1千米的小桶坝有川军旅长谢国嗣家族的“永和”糟坊。在公馆坝岷江河对岸有“小龙灏”和黄伞“欧烤酒”两家糟坊。喜捷是糟坊相当集中的地方,清末民初喜捷街上有5家糟坊。“义盛昌”是由公馆坝徐氏家族后代经营的。“徐洪泰”糟坊也是公馆坝徐氏家族糟坊的分支。黄万兴“汉记”糟坊,兼卖“寡二两”,黄万兴是新中国成立前的乡长黄世模的本家,他的糟坊的背后是喜捷上码头,就在饶德兴饭店的旁边。喜捷场川主庙隔壁的兰尔成糟坊及任顺糟坊也很有名。公馆坝一带酿酒除用地穴式窖池发酵外,酿制小曲酒时,还使用大木桶来代替地穴窖作发酵之所。公馆坝附近岷江两岸这10家糟坊均靠近岷江,兼有运输和汲水之便。民国时期高场有“谢家海”“连平章”“罗烤酒”“刘烤酒”和“唐烤酒”5家糟坊。这些糟坊凭借地处岷江航道和岷江水步道上的有利位置,借助传统酿酒技术的优势,在民国时期盛极一时。
1926~1936年,宜宾县安边场上共有糟坊15家,每家每天煮粮食(主要为苞谷)500斤,产酒一百七八十斤,当场销完(场期3天)。除供应本地外,还外销横江、楼东等地。粮食主要来自本地乡村,屏山、横江的粮食每次以万斤计运销安边,以供酿酒需要。酒糟坊附带喂猪,肥猪除供应本地外,还销到宜宾,卖后再买回所需货物。而在另一川滇边界重要集镇横江场上,有“鼎康”“德华丰”“兴隆号”“纯记”“润记”和“炳记”等7家糟坊。场上酒家更多,烤酒不停仍无法满足需求,还需从安边调酒和柏溪调酒来供应。
南溪与宜宾相邻,水陆交通发达,是主要的酿酒原料产地,酿酒工艺代代传承,一直是宜宾酒的重要供应地之一。清代南溪的酿酒业即十分发达。20世纪40年代,南溪有糟坊113家,设245个桶、年产高粱酒2100吨,几家运销大户酒的日出境量为2吨以上。县城内也以有9家糟坊、3家栈房的广福街为集散点,农村以李庄、留宾、仙临、大观和牟坪等乡镇酿酒最为著名。规模较大的酿酒户有肖质彬、王友荣、王海臣、郎子贤等,均是三代以上以酿酒为业。
宜宾市其他县的酿酒业也十分兴盛,有大量的酿酒作坊,例如高县、庆符县(今庆符镇)在1949年有59户糟坊,珙县在民国时期最多有60家糟坊,江安城区在新中国成立前有规模的糟坊就有5家。2012年3月,根据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承担的国家文物局“指南针计划”专项项目计划的工作要求,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宜宾市博物院,对宜宾地区2区8县50多个乡镇的古代酿酒作坊、遗址进行了初步调查,此次调查的大部分酿酒作坊和遗址均为民国时期。随着历史的发展,很多糟坊已湮没无闻,调查时也已很难查找到,现选择几处分布较为密集的地区做简要介绍。
高县沙河镇 沙河镇是高县地区早期贸易较频繁的集镇,位于镇上双桥街的望马酒厂,和望马酒厂相毗邻,在民国时期原为一家糟坊,新中国成立后收归国有,改革开放后又被私人收购,现仍为传统的前店后坊形式。据作坊酿酒师傅介绍,望马酒厂的几口圆筒形窖池为民国时期的老窖池,而望马山酒厂的老窖池已不存,现在用的窖池是后期用水泥新建的。另外,当地不少群众都提及新由国成立前街上糟坊很多,但现都成为一般民居房,而知详情者大都已过世。由此可见,沙河镇酿酒活动在民国时期是相当发达的。
珙县王家镇 位于珙县南端,东南与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接壤,为五尺道途经之地。川滇两地在此镇有较早的互市传统,商贸活动发达,为酿酒业的发展提供了充分条件。王家老酒建于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后收归国有,破产后为私人购买,现主要生产苞谷酒。现作坊建筑为新中国成立后重建,酒窖为长方形砖砌窖池,蒸灶年代较早。摊场为木板搭建,木板上部放粮食,底部中空,一侧放电扇起到加快通风的作用,同于宜宾县、南溪县一些作坊的做法。另外,此地还有民国时期的王家老酒厂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王家酒厂两家较早的酿酒作坊。一些当地干部和群众都提及早年此地酿酒作坊较多,且在酿造方法上受云南地区影响,体现出一定的地域特色。
屏山县龙华镇 共调查到3处民国时期家庭作坊遗址,现均已停产,且窖池等设备皆不存。其中,龙氏和冉氏两家古屋仍在。据后人介绍,当年糟坊为前店后坊的形式,随着家庭人口增多等原因,后边的作坊也改为居住房,所以窖池等已不存。而另一家唐氏糟坊现已成为一片玉米地,不排除地下仍有部分酿酒遗迹的可能性。
(2)民国时期宜宾酒业经济的特点
民国时期宜宾市酿酒业十分兴盛,酒肆林立,酒业经济发展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宜宾全市酿酒业兴盛发展,出现大量的酿酒作坊,糟坊多以前店后厂的方式经营,这一时期是宜宾酿酒业的大发展阶段,酿酒工艺日益提升。
2.杂粮酒酿造技术改进,促使“五粮液”酒诞生。曲酒酿造在这一时期得到陕西人酿酒技术的支持,叙州酿酒业大力发展,时至清代已有多家大型酿酒坊并存。市场竞争使得各家在酿酒事业上开始注重品质和技术的革新,“利川永”的邓子均就前代得来的“陈氏秘方”,对九种杂粮酿制的杂粮酒进行多次改进,最终采用高粱、大米、糯米、麦子、玉米五种粮食为原料,酿造出香味纯浓的“杂粮酒”,被晚清举人命名为“五粮液”,并成为闻名天下的名酒。
3.民国时期宜宾白酒开始走出国门,也开始具有品牌意识,1915年,邓子均通过上海“利川东”商行,将五粮液送抵太平洋彼岸的美国旧金山万国博览会,使五粮液首次香飘国际。1932年,五粮液印制了第一枚商标,并附带英文开始外销。